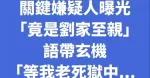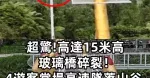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有些真相,讓人不寒而慄

3/3
▲真假太子案成為清軍攻下江南的一個由頭。圖源:影視劇照
南、北兩起「太子案」終結後,歷史上再無關於太子朱慈烺的任何消息。但是,崇禎剩下的兩個皇子——三皇子和四皇子,尤其是三皇子,開始以影子的形式頻繁活躍在反清復明的舞台上。
這就是所謂的「朱三太子」——清朝入關七八十年間,一個最神秘的政治敵人。
據不完全統計,自順治至雍正中期,帝國內部打著「朱三太子」之名起義、謀反或行騙的事件,至少發生了20起。其中最大的幾起,都發生在康熙朝,這正是康熙對陳四一類的群體流民十分敏感和厭惡的原因,搞不好這又是一起「朱三太子」式的謀亂。康熙對「朱三太子」的記憶太深刻了,他曾說,在他在位期間,「匪類稱朱三者甚多」。
隨著明亡的年月越來越遠,民間對崇禎之子的排序和名號的記憶也越來越模糊。起事者自稱「朱三太子」,有時候指的是皇三子,但大多時候指的其實是皇四子。他們給「朱三太子」安的名字也千奇百怪,都是叫朱慈×,但幾乎沒有一個是一樣的。有的叫朱慈璊,有的叫朱慈英,靠譜一點的,叫朱慈炯、朱慈焯、朱慈煥、朱慈焞等等,這些至少知道明朝皇室子孫起名都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做偏旁,崇禎的兒子輪到用「火」字旁。
順治十三年(1656年),直隸真定出現了一個自稱是「朱三太子」的人,他說自己叫朱慈焞。這個「朱三太子」亦欲舉事抗清,先搞廟會集資,香客按照未來明朝光復後的官職捐獻相應價碼的香火錢。結果,兩個捐了未來七品縣令的人因為爭搶道路大打出手,把整個反清復明的大計劃捅到了官府。自稱朱慈焞的「朱三太子」隨後被處死。
類似事件在順治朝發生多起,但相比當時的南明政權,這些「朱三太子事件」給清朝造成的影響並不大。康熙繼位後,除了台灣的鄭氏集團堅持抗清之外,清廷基本實現了對明朝疆域的全面征服,此後,以「朱三太子」為旗號反清復明的事件越來越多,影響也越來越大。
康熙十二年(1673年)十一月二十一日,吳三桂在雲南起兵,揚言要在明年元旦把朱三太子推上帝位。
一個月後,消息傳至北京,漢人楊起隆偽稱自己就是「朱三太子」,並組織了千人規模的八旗漢人奴僕起義隊伍,起義者自稱「中興官兵」,建年號「廣德」,以頭裹白布、身束紅帶為標誌,約定十二月二十三日五更時分在「京城內外,放火舉事」。因消息走漏,楊起隆提前一天倉促起事。
康熙獲悉這起發生在天子腳下的「朱三太子事件」,極為震驚,命令關閉京師九門,緝拿起義者。史書記載,「獲賊既多,斬頭無地,以車滿載出九門斬之,屍積如山,如是者八日」。
楊起隆隨後成為僅次於三藩之亂首領人物的特級通緝犯,康熙一刻也不放鬆對他的緝捕。大約七年後,陝西漢中緝拿了一個自稱「朱三太子」的人,又稱自己就是楊起隆。康熙卻認定,此人既不是朱三太子,也不是楊起隆,僅是楊起隆起義隊伍中的一個逃犯,後來託名造反而已。又過了兩年,康熙還不忘提醒帝國官員,別忘了緝拿楊起隆的事。可見這個偽「朱三太子」在康熙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陰影。
康熙十六年(1677年),福建漳州人蔡寅自稱「朱三太子」,組織「白頭軍」抗清。
康熙十八年(1679年),清軍在湖南新化縣一座寺廟內俘獲了一個自稱「明朝太子朱慈燦」的人。此人自述曾隨李自成敗軍離京,後在河南出家為僧,流落江西、湖廣20餘年,因病還俗。康熙為此專門詢問過明朝的老太監,最後含糊地認定「大約是假」,並將其處死。
對於此起彼伏的、大大小小的「朱三太子事件」,康熙一概十分關注,並親自介入。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或許從未現身,但已經在帝國的統治者心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夢魘。
康熙四十七年(1708年),一個可能是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被捕了。
事情源於浙江的一起反清復明起義。張念一以「朱三太子」的名義起事,建年號「大明天德」,揚言「朱三太子要復中原」。起義失敗後,張念一被捕,清廷在審訊中獲悉一個可能是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長期生活在江浙一帶。於是,一張緝捕之網悄然張開。
大約兩個月後,山東巡撫報告,在境內緝獲了「朱三太子」。被捕後,「朱三太子」供稱,他已改名王士元,「原姓朱,是明朝後裔,排行第四,叫慈煥,我二哥哥早死了,我與三哥哥同歲,自十歲上就離開了」。
據其供述,當年,李自成大順軍自北京敗退後,朱慈煥流落到安徽鳳陽,偶遇一名姓王的明朝給事中,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,王收養了他,並為他改名王士元,隨其子弟讀書。朱慈煥十九歲時,王家突遭變故,朱慈煥再度流落江湖,幾年後,他娶了胡姓女子為妻,落戶浙江餘姚,在家開設私塾,人稱「王老先生」。
朱慈煥曾向密友透露過他非同尋常的身份,消息由此傳開來。張念一等人得知後,遂擁戴這個「朱三太子」反清,這讓朱慈煥很害怕,從起義一開始就四處躲藏。期間,他的妻妾、女兒、兒媳等人因官府通緝而上吊,三個兒子也被捕。他本人被捕後供述:「我從沒有非分之想。遇見他們要妄為的人,我惟有躲避了,因勸不住他們,所以躲到山東,苟延殘喘而已。」
在康熙的授意下,清廷對這個「朱三太子」的審訊規格定得非常高。朱慈煥祖孫三代七人被押解到京城,由九卿會審。
當時,朱慈煥已經75歲高齡,他對主審官員說:「吾今年七十五歲,血氣已衰,鬢髮皆白,乃不作反於三藩叛亂之時,而反於清寧無事之日乎?且所謂謀反者,必占據城池,積草屯糧,招買軍馬,打造軍器,吾曾有一此乎?」
刑部認定他未參與謀反之事,但又下定論說:「朱某雖無謀反之事,未嘗無謀反之心。」
然而,最終的定罪,卻與謀不謀反無關。
幾名大學士在聯合審訊後,由張廷玉結案上奏說:「王士元自認崇禎第四子,查崇禎第四子已於崇禎十四年身故,又遵旨傳喚明代老太監,俱不認識。王士元明系假冒,其父子俱應凌遲處死。」
康熙要朱慈煥死,底下人自然明白怎麼操作——假冒前朝皇子,這個罪名既能讓清廷擺脫嚴苛無情的罵名,又能讓不管真真假假的帝國潛在敵人消弭於無形。正如孟森所說:「以前朝皇子非罪名,務令以假冒為罪。」真是前朝皇子,那是沒罪的,按清廷宣稱的政策還必須優待,所以一定要說他是假冒前朝皇子,這樣才能定罪。
就這樣,75歲的朱慈煥被凌遲處死,他的兒孫也被殺。整個家族遭遇了滅頂之災,無一倖存。
後來,清廷在修《明史》的時候,為了掩蓋被殺的朱慈煥的真實身份,在崇禎幾個兒子的排序和名字上做了手腳。朱慈煥自供是崇禎第四子,《明史》卻記載崇禎第四子為朱慈炤,第五子為朱慈煥。因第五子早夭的事實眾所周知,清廷就可順勢擺脫殺害朱慈煥的嫌疑,而進一步坐實康熙四十七年凌遲處死的這個「朱慈煥」是個冒牌貨。這就是我前面所講的,歷史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權力,它可以掩蓋一些事實,也可以製造另一些事實。
總之,康熙四十七年的朱慈煥之死,是清朝入關以來「朱三太子」最接近真實的一次現身了。此後,民間仍以「朱三太子」為反清復明的象徵,但通通都是假託其名而已。
1644年清廷入關,對明朝臣民宣布:「義師為爾復君父仇。」我們是替明朝復仇來的,明清的共同敵人是李自成的農民軍。這個口號很有迷惑性,一開始頗得明朝臣民的認可,連南明弘光朝都曾計劃與清軍聯手打農民軍。
與「替明朝復仇論」相配套的是,清廷多次宣稱禮遇和優待明朝皇室子孫。這是順理成章的,你想啊,不可能我說替你報仇,完了把你全家都做了吧,這樣狼子野心全暴露了,還怎樣取信天下!
順治在即位詔中,承諾明朝宗室貴族「首倡投誠,先來歸順,赴京朝見者,仍給祿養」,只要跟了我,你們的待遇不變,跟明朝一樣。清軍攻克南京後,重申「遇明朝子孫,素從優厚」。
康熙也曾在南巡期間,親自祭拜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,看到陵寢損壞嚴重,無人專職看守,遂表態說:「朕意欲訪察明代後裔,授以職銜,俾其世守祀事。」
但事實上,由於明朝實行同姓貴族分封制,皇室成員眾多,且在各地擁有巨大的政治和經濟特權,南明各政權正是擁戴各個宗室成員建立起來的。所以,清廷對明朝宗室勢力頗為忌憚,表面上宣稱要優待,要尋訪後裔供起來,背地裡卻對有實力、有身份而可能對其統治構成威脅的明皇室成員採取了斬草除根計劃。
怎樣不動聲色地斬草除根,這是個技術活兒。
康熙拜祭完明孝陵,交代當地尋找明代後裔,地方官最終以「雖經查訪,亦難得實」——找了,但明代後裔身份無法核實——而作罷。這是一種人畜無害的說辭,既顧全了皇帝的體面,又不至於真的找個明代後裔供起來,成為民間反清復明的象徵。
然而,更多的時候,清廷採用的是「假冒」的罪名,將真真假假的明代宗室成員,一概置於死地。
真身一旦出現,按照清廷宣稱的政策,不僅不能加害,還要禮遇優待。這是清廷不願意承受的結果。因此,不管真假,一概認定為假,這就有了正當殺害的理由,一勞永逸。這就是清廷的如意算盤。上文講到的所有「明太子案」「朱三太子案」,全部被清廷公開認定為「偽太子」「偽朱三太子」並處死,原因在這裡。僅有多鐸攻下南京後,一度為了政治需要宣稱南京那個王之明是「真太子」,但很快,「真太子」進京後被覆案,重新認定為「偽太子」,匆匆處死。
不僅是各種名目的末代皇子被「打假」,連明朝宗室,清廷也以「打假」之名進行殺害。
明朝永安王宗室朱華塘,封鎮國將軍。順治二年(1645年),多鐸兵臨江南,朱華塘投降後,攜清廷恩詔一紙赴湖廣招撫,見族中宗室俱已投順,自己便在九華山出家。後外出化緣,在江西九江被捕。朱華塘當時已經79歲高齡,「衰病垂危」,但清廷仍以「詐傳親王令旨」罪將其處死。一個「詐」字,說明清廷認定這個朱華塘是冒牌貨,跟後來康熙時期處死朱慈煥的操作,如出一轍。
明亡後,明朝宗室朱應龍出家為道,改名王道真,暗地裡招募英雄好漢,密謀「恢復故業」,後被陝西平涼府捕獲。被捕後,朱應龍只揖不跪,自供身世說是「天啟東宮太子」。儘管王道真供述東宮太子細節甚詳,但清廷仍以「詐稱天啟東宮」罪將其處死。
但是,問題也來了。
清廷自以為以「假冒」之名可以從肉體上消除明朝宗室敵對力量,卻沒想到,由於那些「真身」遲遲未被認定,導致後續有無數的「真身」冒出來。「朱三太子」在清朝入關後80年內層出不窮,成為孟森所說的社會反清復明的一種「公名」,正是因為清廷從未承認其中任何一個人是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,所以民間始終相信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還活在人間。這就叫「假作真時真亦假」,真真假假,官民雙方都可以從自身立場出發進行闡釋,各取所需。
假如清廷從一開始就「以假為真」,認定具體的一個人為「朱三太子」,那麼,哪怕真正的朱三太子現身了,他也難以自證為真,「朱三太子」這個名號的能量想必就會小很多,不至於折磨了清朝幾十年。
儘管雍正中期以後,「朱三太子」再未出沒(此時「朱三太子」要在世,已經年近百歲,打他的旗號,有違人壽的常識),但「朱三太子案」後遺症,仍然深深籠罩在雍正心中。雍正在他的《大義覺迷錄》中說:「從來異姓先後繼統,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,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。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,搖惑人心若此之眾者。」
到了乾隆時期,一個虛構的人物——朱洪英取代「朱三太子」開始走紅,成為反清復明的象徵性人物。天地會的起源傳說中,就主打朱洪英要復興明朝的點,作為吸納會眾的共同記憶。這也算是「朱三太子」留給乾隆的一個惡夢,終其一生,他像他的祖父和父親一樣,對各種可能存在的聚眾謠言和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妖術,都十分恐懼,必欲徹查追問到底。
康雍乾三代皇帝在所謂的盛世中,大興文字獄,也是這種政治性夢魘在作祟。
而大清兩百多年,所有的帝王都活在一種惘惘的威脅中,直至它覆滅為止。這已經說不清是歷史的幽靈,還是權力的心魔了。
南、北兩起「太子案」終結後,歷史上再無關於太子朱慈烺的任何消息。但是,崇禎剩下的兩個皇子——三皇子和四皇子,尤其是三皇子,開始以影子的形式頻繁活躍在反清復明的舞台上。
這就是所謂的「朱三太子」——清朝入關七八十年間,一個最神秘的政治敵人。
據不完全統計,自順治至雍正中期,帝國內部打著「朱三太子」之名起義、謀反或行騙的事件,至少發生了20起。其中最大的幾起,都發生在康熙朝,這正是康熙對陳四一類的群體流民十分敏感和厭惡的原因,搞不好這又是一起「朱三太子」式的謀亂。康熙對「朱三太子」的記憶太深刻了,他曾說,在他在位期間,「匪類稱朱三者甚多」。
隨著明亡的年月越來越遠,民間對崇禎之子的排序和名號的記憶也越來越模糊。起事者自稱「朱三太子」,有時候指的是皇三子,但大多時候指的其實是皇四子。他們給「朱三太子」安的名字也千奇百怪,都是叫朱慈×,但幾乎沒有一個是一樣的。有的叫朱慈璊,有的叫朱慈英,靠譜一點的,叫朱慈炯、朱慈焯、朱慈煥、朱慈焞等等,這些至少知道明朝皇室子孫起名都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做偏旁,崇禎的兒子輪到用「火」字旁。
順治十三年(1656年),直隸真定出現了一個自稱是「朱三太子」的人,他說自己叫朱慈焞。這個「朱三太子」亦欲舉事抗清,先搞廟會集資,香客按照未來明朝光復後的官職捐獻相應價碼的香火錢。結果,兩個捐了未來七品縣令的人因為爭搶道路大打出手,把整個反清復明的大計劃捅到了官府。自稱朱慈焞的「朱三太子」隨後被處死。
類似事件在順治朝發生多起,但相比當時的南明政權,這些「朱三太子事件」給清朝造成的影響並不大。康熙繼位後,除了台灣的鄭氏集團堅持抗清之外,清廷基本實現了對明朝疆域的全面征服,此後,以「朱三太子」為旗號反清復明的事件越來越多,影響也越來越大。
康熙十二年(1673年)十一月二十一日,吳三桂在雲南起兵,揚言要在明年元旦把朱三太子推上帝位。
一個月後,消息傳至北京,漢人楊起隆偽稱自己就是「朱三太子」,並組織了千人規模的八旗漢人奴僕起義隊伍,起義者自稱「中興官兵」,建年號「廣德」,以頭裹白布、身束紅帶為標誌,約定十二月二十三日五更時分在「京城內外,放火舉事」。因消息走漏,楊起隆提前一天倉促起事。
康熙獲悉這起發生在天子腳下的「朱三太子事件」,極為震驚,命令關閉京師九門,緝拿起義者。史書記載,「獲賊既多,斬頭無地,以車滿載出九門斬之,屍積如山,如是者八日」。
楊起隆隨後成為僅次於三藩之亂首領人物的特級通緝犯,康熙一刻也不放鬆對他的緝捕。大約七年後,陝西漢中緝拿了一個自稱「朱三太子」的人,又稱自己就是楊起隆。康熙卻認定,此人既不是朱三太子,也不是楊起隆,僅是楊起隆起義隊伍中的一個逃犯,後來託名造反而已。又過了兩年,康熙還不忘提醒帝國官員,別忘了緝拿楊起隆的事。可見這個偽「朱三太子」在康熙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陰影。
康熙十六年(1677年),福建漳州人蔡寅自稱「朱三太子」,組織「白頭軍」抗清。
康熙十八年(1679年),清軍在湖南新化縣一座寺廟內俘獲了一個自稱「明朝太子朱慈燦」的人。此人自述曾隨李自成敗軍離京,後在河南出家為僧,流落江西、湖廣20餘年,因病還俗。康熙為此專門詢問過明朝的老太監,最後含糊地認定「大約是假」,並將其處死。
對於此起彼伏的、大大小小的「朱三太子事件」,康熙一概十分關注,並親自介入。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或許從未現身,但已經在帝國的統治者心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夢魘。
康熙四十七年(1708年),一個可能是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被捕了。
事情源於浙江的一起反清復明起義。張念一以「朱三太子」的名義起事,建年號「大明天德」,揚言「朱三太子要復中原」。起義失敗後,張念一被捕,清廷在審訊中獲悉一個可能是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長期生活在江浙一帶。於是,一張緝捕之網悄然張開。
大約兩個月後,山東巡撫報告,在境內緝獲了「朱三太子」。被捕後,「朱三太子」供稱,他已改名王士元,「原姓朱,是明朝後裔,排行第四,叫慈煥,我二哥哥早死了,我與三哥哥同歲,自十歲上就離開了」。
據其供述,當年,李自成大順軍自北京敗退後,朱慈煥流落到安徽鳳陽,偶遇一名姓王的明朝給事中,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,王收養了他,並為他改名王士元,隨其子弟讀書。朱慈煥十九歲時,王家突遭變故,朱慈煥再度流落江湖,幾年後,他娶了胡姓女子為妻,落戶浙江餘姚,在家開設私塾,人稱「王老先生」。
朱慈煥曾向密友透露過他非同尋常的身份,消息由此傳開來。張念一等人得知後,遂擁戴這個「朱三太子」反清,這讓朱慈煥很害怕,從起義一開始就四處躲藏。期間,他的妻妾、女兒、兒媳等人因官府通緝而上吊,三個兒子也被捕。他本人被捕後供述:「我從沒有非分之想。遇見他們要妄為的人,我惟有躲避了,因勸不住他們,所以躲到山東,苟延殘喘而已。」
在康熙的授意下,清廷對這個「朱三太子」的審訊規格定得非常高。朱慈煥祖孫三代七人被押解到京城,由九卿會審。
當時,朱慈煥已經75歲高齡,他對主審官員說:「吾今年七十五歲,血氣已衰,鬢髮皆白,乃不作反於三藩叛亂之時,而反於清寧無事之日乎?且所謂謀反者,必占據城池,積草屯糧,招買軍馬,打造軍器,吾曾有一此乎?」
刑部認定他未參與謀反之事,但又下定論說:「朱某雖無謀反之事,未嘗無謀反之心。」
然而,最終的定罪,卻與謀不謀反無關。
幾名大學士在聯合審訊後,由張廷玉結案上奏說:「王士元自認崇禎第四子,查崇禎第四子已於崇禎十四年身故,又遵旨傳喚明代老太監,俱不認識。王士元明系假冒,其父子俱應凌遲處死。」
康熙要朱慈煥死,底下人自然明白怎麼操作——假冒前朝皇子,這個罪名既能讓清廷擺脫嚴苛無情的罵名,又能讓不管真真假假的帝國潛在敵人消弭於無形。正如孟森所說:「以前朝皇子非罪名,務令以假冒為罪。」真是前朝皇子,那是沒罪的,按清廷宣稱的政策還必須優待,所以一定要說他是假冒前朝皇子,這樣才能定罪。
就這樣,75歲的朱慈煥被凌遲處死,他的兒孫也被殺。整個家族遭遇了滅頂之災,無一倖存。
後來,清廷在修《明史》的時候,為了掩蓋被殺的朱慈煥的真實身份,在崇禎幾個兒子的排序和名字上做了手腳。朱慈煥自供是崇禎第四子,《明史》卻記載崇禎第四子為朱慈炤,第五子為朱慈煥。因第五子早夭的事實眾所周知,清廷就可順勢擺脫殺害朱慈煥的嫌疑,而進一步坐實康熙四十七年凌遲處死的這個「朱慈煥」是個冒牌貨。這就是我前面所講的,歷史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權力,它可以掩蓋一些事實,也可以製造另一些事實。
總之,康熙四十七年的朱慈煥之死,是清朝入關以來「朱三太子」最接近真實的一次現身了。此後,民間仍以「朱三太子」為反清復明的象徵,但通通都是假託其名而已。
1644年清廷入關,對明朝臣民宣布:「義師為爾復君父仇。」我們是替明朝復仇來的,明清的共同敵人是李自成的農民軍。這個口號很有迷惑性,一開始頗得明朝臣民的認可,連南明弘光朝都曾計劃與清軍聯手打農民軍。
與「替明朝復仇論」相配套的是,清廷多次宣稱禮遇和優待明朝皇室子孫。這是順理成章的,你想啊,不可能我說替你報仇,完了把你全家都做了吧,這樣狼子野心全暴露了,還怎樣取信天下!
順治在即位詔中,承諾明朝宗室貴族「首倡投誠,先來歸順,赴京朝見者,仍給祿養」,只要跟了我,你們的待遇不變,跟明朝一樣。清軍攻克南京後,重申「遇明朝子孫,素從優厚」。
康熙也曾在南巡期間,親自祭拜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,看到陵寢損壞嚴重,無人專職看守,遂表態說:「朕意欲訪察明代後裔,授以職銜,俾其世守祀事。」
但事實上,由於明朝實行同姓貴族分封制,皇室成員眾多,且在各地擁有巨大的政治和經濟特權,南明各政權正是擁戴各個宗室成員建立起來的。所以,清廷對明朝宗室勢力頗為忌憚,表面上宣稱要優待,要尋訪後裔供起來,背地裡卻對有實力、有身份而可能對其統治構成威脅的明皇室成員採取了斬草除根計劃。
怎樣不動聲色地斬草除根,這是個技術活兒。
康熙拜祭完明孝陵,交代當地尋找明代後裔,地方官最終以「雖經查訪,亦難得實」——找了,但明代後裔身份無法核實——而作罷。這是一種人畜無害的說辭,既顧全了皇帝的體面,又不至於真的找個明代後裔供起來,成為民間反清復明的象徵。
然而,更多的時候,清廷採用的是「假冒」的罪名,將真真假假的明代宗室成員,一概置於死地。
真身一旦出現,按照清廷宣稱的政策,不僅不能加害,還要禮遇優待。這是清廷不願意承受的結果。因此,不管真假,一概認定為假,這就有了正當殺害的理由,一勞永逸。這就是清廷的如意算盤。上文講到的所有「明太子案」「朱三太子案」,全部被清廷公開認定為「偽太子」「偽朱三太子」並處死,原因在這裡。僅有多鐸攻下南京後,一度為了政治需要宣稱南京那個王之明是「真太子」,但很快,「真太子」進京後被覆案,重新認定為「偽太子」,匆匆處死。
不僅是各種名目的末代皇子被「打假」,連明朝宗室,清廷也以「打假」之名進行殺害。
明朝永安王宗室朱華塘,封鎮國將軍。順治二年(1645年),多鐸兵臨江南,朱華塘投降後,攜清廷恩詔一紙赴湖廣招撫,見族中宗室俱已投順,自己便在九華山出家。後外出化緣,在江西九江被捕。朱華塘當時已經79歲高齡,「衰病垂危」,但清廷仍以「詐傳親王令旨」罪將其處死。一個「詐」字,說明清廷認定這個朱華塘是冒牌貨,跟後來康熙時期處死朱慈煥的操作,如出一轍。
明亡後,明朝宗室朱應龍出家為道,改名王道真,暗地裡招募英雄好漢,密謀「恢復故業」,後被陝西平涼府捕獲。被捕後,朱應龍只揖不跪,自供身世說是「天啟東宮太子」。儘管王道真供述東宮太子細節甚詳,但清廷仍以「詐稱天啟東宮」罪將其處死。
但是,問題也來了。
清廷自以為以「假冒」之名可以從肉體上消除明朝宗室敵對力量,卻沒想到,由於那些「真身」遲遲未被認定,導致後續有無數的「真身」冒出來。「朱三太子」在清朝入關後80年內層出不窮,成為孟森所說的社會反清復明的一種「公名」,正是因為清廷從未承認其中任何一個人是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,所以民間始終相信真正的「朱三太子」還活在人間。這就叫「假作真時真亦假」,真真假假,官民雙方都可以從自身立場出發進行闡釋,各取所需。
假如清廷從一開始就「以假為真」,認定具體的一個人為「朱三太子」,那麼,哪怕真正的朱三太子現身了,他也難以自證為真,「朱三太子」這個名號的能量想必就會小很多,不至於折磨了清朝幾十年。
儘管雍正中期以後,「朱三太子」再未出沒(此時「朱三太子」要在世,已經年近百歲,打他的旗號,有違人壽的常識),但「朱三太子案」後遺症,仍然深深籠罩在雍正心中。雍正在他的《大義覺迷錄》中說:「從來異姓先後繼統,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,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。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,搖惑人心若此之眾者。」
到了乾隆時期,一個虛構的人物——朱洪英取代「朱三太子」開始走紅,成為反清復明的象徵性人物。天地會的起源傳說中,就主打朱洪英要復興明朝的點,作為吸納會眾的共同記憶。這也算是「朱三太子」留給乾隆的一個惡夢,終其一生,他像他的祖父和父親一樣,對各種可能存在的聚眾謠言和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妖術,都十分恐懼,必欲徹查追問到底。
康雍乾三代皇帝在所謂的盛世中,大興文字獄,也是這種政治性夢魘在作祟。
而大清兩百多年,所有的帝王都活在一種惘惘的威脅中,直至它覆滅為止。這已經說不清是歷史的幽靈,還是權力的心魔了。
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