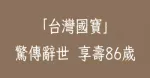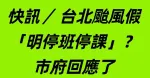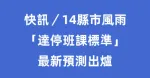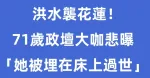4/4
下一頁
1905年秋瑾和魯迅激烈爭辯,秋瑾拔刀插在講台上,丟下一句狠話

4/4
她當晚即乘船返國,再無遲疑。
那一日東京的雪,許多人終生難忘,有人說她太過衝動,也有人說她是「孤勇者」,但更多的人,是在她離開後的沉默中,開始重新思考「革命」的真正含義。
後來,魯迅曾在回憶中說:「她直爽、幹練,朋友之間無人不喜。」
他也曾悼念她,以小說人物「夏瑜」緬懷她的犧牲。
可那一日講台上的短刀,終究割裂了他們彼此間最後的默契。
熱血未涼
歸國的船靠岸時,秋瑾披著一身風霜。
她仿佛不是歸來的人,而是歸位的將軍。
她早不再是官宦人家的女兒,不再是溫婉賢淑的王家媳婦,她是「秋大俠」,是中國婦女獨立意識覺醒的引領者,是即將燃起革命戰火的火種之一。
回到上海,她沒有絲毫休整便投入革命籌備之中。
她將東京積攢的稿件重新整理,幾經奔走,籌得資金後創辦了《中國女報》。
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完全由女性主編的報紙,其宗旨鮮明:
「女學不興,種族不強;女權不振,國勢必弱。」
報紙上的每一個字、每一句話,都在質問舊時代,也在喚醒沉睡中的同胞。
為了辦報籌資,她甚至回到娘家募捐。
家人望著她的裝束與目光,無不震驚,有人勸她:
「瑾兒,回家吧,別再做這些無人理解的事了。」
秋瑾平靜地回道:「若是人人都等別人理解,那這世上何來改天換地之人?」
與此同時,她在紹興創辦了中國公學和女學堂,親自任教,一手提筆,一手握劍。
她不只傳授知識,更傳播革命思想。
她告訴那些仍然身著束衣、滿臉懵懂的女學生:
「你們不是誰的附庸,也不是誰的玩偶,你們是國家未來的一半,是中華脊樑的一翼。」
除了辦學與辦報,她更積極串聯革命志士,加入同盟會,聯絡各地響應志士。
她常年奔走於上海、杭州、紹興之間,衣不解帶,常以男裝示人,腳步堅定如鐵。
她策劃浙江起義,擬定檄文、安排軍械、傳遞密信,一步步將革命推向高潮。
她還親自聯繫光復會、共進會等革命團體,商定進攻方案,甚至不惜以自己為餌,吸引清廷注意,好為其他同志爭取更多準備時間。
1907年,浙江起義在即,她計劃從金華起事,一路北上,打通浙皖門戶。
為此她親自編排《革命軍》宣傳資料,四處分發,白日授課,夜晚策劃。
那些日子,她每日只睡兩三個時辰,靠濃茶與藥酒強撐精神。
有人勸她休息,她卻笑言:「刀未出鞘,哪敢松弦?」
但理想從來不敵風雨驟變。
六月,安慶起義失敗的消息傳來,如晴天霹靂擊在秋瑾心頭。
她知道,一切都可能暴露,革命的火線已然燃至眼前。
紹興當地清軍已接到緝捕命令,三百兵丁正疾馳而來。
她沒有選擇逃亡,而是選擇迎戰。
她第一時間指揮學生銷毀文書、藏匿槍械,分散撤離。
隨後,她一個人坐在大通學堂的大堂內,靜候清兵。
她甚至從容地為那些女學生準備了路費,將最後一批銀元分發完畢,才緩緩坐回椅中。
有人問她:「先生,你為何不走?」
她輕聲回答:「若我今日走了,何以面對天下後人?」
熱血未涼,烈火未熄,我願為炬,照亮前路。
生死訣別
那一天,秋瑾沒有合眼,而是提筆寫下絕命詩:
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。」
這短短七字,是她一生的收束,也是整個時代的嘆息。
她未寫「痛」,未寫「死」,只用兩個最輕盈的自然意象,訴盡臨終之哀。
愁,是她為家國、為未竟的理想、為被吞沒的風骨所留下的淚;煞人,是她無奈之中,依然擲地有聲的吶喊。
清兵破門而入之時,秋瑾仍端坐堂中。
沒有掙扎、沒有哀求,她甚至未回頭望一眼那盞燈。
她未交代姓名、未供出同黨,只靜靜地看著將士封鎖她書桌、帶走她所剩不多的財物。
7月15日凌晨,她在紹興軒亭口赴義,沒有哭喊,沒有掙扎,只有一身素衣,和眉眼間的從容。
她的死,迅速傳遍江南。
報館爭相登載,詩人頻頻悼念,她的照片與詩文刊印成冊,在文人圈、在學術圈、在留學生圈廣泛流傳。
一個女子,一場公然的犧牲,震撼了無數原本沉默的人心。
在數千里之外的東京,魯迅得知此事的那一夜,據說沉默良久。
他曾與她爭論,曾與她針鋒相對,可他始終敬重她。
多年之後,他寫下小說《藥》,那是他用筆為刀的第一聲吶喊,他要把她的血,化作千千萬萬人的覺醒。
秋瑾與魯迅,最終走上了兩條不一樣的路。
一人燃燒如炬,一人冷峻如刃;一人以死震世,一人以文喚魂。
可他們的目標,卻從未偏離,那就是喚醒沉睡的中國,讓這個民族重新站起來。
那一日東京的雪,許多人終生難忘,有人說她太過衝動,也有人說她是「孤勇者」,但更多的人,是在她離開後的沉默中,開始重新思考「革命」的真正含義。
後來,魯迅曾在回憶中說:「她直爽、幹練,朋友之間無人不喜。」
他也曾悼念她,以小說人物「夏瑜」緬懷她的犧牲。
可那一日講台上的短刀,終究割裂了他們彼此間最後的默契。
熱血未涼
歸國的船靠岸時,秋瑾披著一身風霜。
她仿佛不是歸來的人,而是歸位的將軍。
她早不再是官宦人家的女兒,不再是溫婉賢淑的王家媳婦,她是「秋大俠」,是中國婦女獨立意識覺醒的引領者,是即將燃起革命戰火的火種之一。
回到上海,她沒有絲毫休整便投入革命籌備之中。
她將東京積攢的稿件重新整理,幾經奔走,籌得資金後創辦了《中國女報》。
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完全由女性主編的報紙,其宗旨鮮明:
「女學不興,種族不強;女權不振,國勢必弱。」
報紙上的每一個字、每一句話,都在質問舊時代,也在喚醒沉睡中的同胞。
為了辦報籌資,她甚至回到娘家募捐。
家人望著她的裝束與目光,無不震驚,有人勸她:
「瑾兒,回家吧,別再做這些無人理解的事了。」
秋瑾平靜地回道:「若是人人都等別人理解,那這世上何來改天換地之人?」
與此同時,她在紹興創辦了中國公學和女學堂,親自任教,一手提筆,一手握劍。
她不只傳授知識,更傳播革命思想。
她告訴那些仍然身著束衣、滿臉懵懂的女學生:
「你們不是誰的附庸,也不是誰的玩偶,你們是國家未來的一半,是中華脊樑的一翼。」
除了辦學與辦報,她更積極串聯革命志士,加入同盟會,聯絡各地響應志士。
她常年奔走於上海、杭州、紹興之間,衣不解帶,常以男裝示人,腳步堅定如鐵。
她策劃浙江起義,擬定檄文、安排軍械、傳遞密信,一步步將革命推向高潮。
她還親自聯繫光復會、共進會等革命團體,商定進攻方案,甚至不惜以自己為餌,吸引清廷注意,好為其他同志爭取更多準備時間。
1907年,浙江起義在即,她計劃從金華起事,一路北上,打通浙皖門戶。
為此她親自編排《革命軍》宣傳資料,四處分發,白日授課,夜晚策劃。
那些日子,她每日只睡兩三個時辰,靠濃茶與藥酒強撐精神。
有人勸她休息,她卻笑言:「刀未出鞘,哪敢松弦?」
但理想從來不敵風雨驟變。
六月,安慶起義失敗的消息傳來,如晴天霹靂擊在秋瑾心頭。
她知道,一切都可能暴露,革命的火線已然燃至眼前。
紹興當地清軍已接到緝捕命令,三百兵丁正疾馳而來。
她沒有選擇逃亡,而是選擇迎戰。
她第一時間指揮學生銷毀文書、藏匿槍械,分散撤離。
隨後,她一個人坐在大通學堂的大堂內,靜候清兵。
她甚至從容地為那些女學生準備了路費,將最後一批銀元分發完畢,才緩緩坐回椅中。
有人問她:「先生,你為何不走?」
她輕聲回答:「若我今日走了,何以面對天下後人?」
熱血未涼,烈火未熄,我願為炬,照亮前路。
生死訣別
那一天,秋瑾沒有合眼,而是提筆寫下絕命詩:
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。」
這短短七字,是她一生的收束,也是整個時代的嘆息。
她未寫「痛」,未寫「死」,只用兩個最輕盈的自然意象,訴盡臨終之哀。
愁,是她為家國、為未竟的理想、為被吞沒的風骨所留下的淚;煞人,是她無奈之中,依然擲地有聲的吶喊。
清兵破門而入之時,秋瑾仍端坐堂中。
沒有掙扎、沒有哀求,她甚至未回頭望一眼那盞燈。
她未交代姓名、未供出同黨,只靜靜地看著將士封鎖她書桌、帶走她所剩不多的財物。
7月15日凌晨,她在紹興軒亭口赴義,沒有哭喊,沒有掙扎,只有一身素衣,和眉眼間的從容。
她的死,迅速傳遍江南。
報館爭相登載,詩人頻頻悼念,她的照片與詩文刊印成冊,在文人圈、在學術圈、在留學生圈廣泛流傳。
一個女子,一場公然的犧牲,震撼了無數原本沉默的人心。
在數千里之外的東京,魯迅得知此事的那一夜,據說沉默良久。
他曾與她爭論,曾與她針鋒相對,可他始終敬重她。
多年之後,他寫下小說《藥》,那是他用筆為刀的第一聲吶喊,他要把她的血,化作千千萬萬人的覺醒。
秋瑾與魯迅,最終走上了兩條不一樣的路。
一人燃燒如炬,一人冷峻如刃;一人以死震世,一人以文喚魂。
可他們的目標,卻從未偏離,那就是喚醒沉睡的中國,讓這個民族重新站起來。
 呂純弘 • 11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