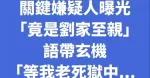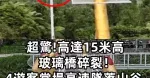1/4
下一頁
《中國禁書》國內封禁,國外封神

1/4
國內封禁,國外封神
用史學家黃仁宇的話來說,萬曆十五年(1587年),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份。
江西人宋應星,就出生在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。
宋應星出生之時,家、國雙衰——比國家衰落得更快的是他的家族。從三代俱封尚書的高光家族,到黯淡無光的普通家族,只用了三四十年。
據說,宋應星少年天才,過目不忘。但這個本事對於他個人命運、家族命運的扭轉,毫無益處。
他一生最大的光榮,就是和哥哥宋應昇在江西鄉試中,雙雙考中舉人。
此後,他五次進京考進士,每次都當了炮灰。
沒辦法,縱有凌雲志,他一輩子也只能苟且在縣城教諭這樣無權無錢的職位上。
但他始終心有不甘,時常沒日沒夜、吭哧吭哧地寫書。
大概50歲的時候,他的書殺青了。這時,他告訴世人:
傷哉,貧也!欲購奇考證,而乏洛下之資;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,而缺陳思之館。隨其孤陋見聞,藏諸方寸而寫之,豈有當哉!
翻譯過來就是,貧窮限制了我,我沒有錢購買參考資料,也沒有條件邀集同人集思廣議,只能寫成這個樣子了,能不傷心嗎?
還好,他有個好朋友塗伯聚,幫他把書印刷出版了。
這一年是1637年。
很多很多年以後,歷史學家說起1637年,總會強調這是一個奇特的年份。這一年,東西方分別出版了一本深刻影響人類歷史的書。
一本是歐洲近代哲學奠基人笛卡爾的《方法論》,另一本,正是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。
令人嗟嘆的是,這兩本偉大之書的命運截然不同。前者樹立起理性主義的大旗,藉助科學實踐掀起產業革命,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。
而後者,卻開啟了一段過山車般的奇幻傳播旅程。
▲宋應星,一個奇人寫了一本奇書。圖源:圖蟲創意授權
宋應星是個奇人。在《天工開物》問世大約300年後,地質學家丁文江如此評價他:
士大夫之心理,內容乾燥荒蕪,等於不毛之沙漠,宋氏獨自辟門徑,一反明儒陋習,就人民日用飲食器具而究其源,其活力之偉,結構之大,觀察之富,有明一代,一人而已。
這幾乎是把宋應星捧上天了。
《天工開物》到底是本什麼書,會讓宋應星贏得「有明一代,一人而已」的極高讚譽?
簡單說,這本書總結了大量農業、工業中所需要的培育、生產知識,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科普體系,並有意識使用數據記載,使整本書更加實用。
西方人稱這本書為「中國十七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」。
這本書初版時,在國內的銷量並不好。沒幾年,大明亡了。清初,有個叫楊素卿的福建書商發現了這本書,並把他包裝成了暢銷書。
當時很多人因此知道並讀到《天工開物》。
宋應星撰述此書,目的是通過實學,來達到富國強民。他的骨子裡還是有為時代把脈,並開出藥方的想法。
晚明的思想、經濟以及科技發展勢頭,實際上並不落後於西歐。當時,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產生,一些思想家呼籲人性解放,另一些人倡導實用主義,擺脫既往的道德話語束縛,不再將科學技術視為「奇技淫巧」。
他們通過田野考察、收集整理、記錄數據、歸納分類等方法,寫出了一批科技著作。比如,地理學有徐霞客的《遊記》,藥物學有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,水利工程有潘季馴的《河防一覽》,農學有徐光啟的《農政全書》等等。
大家公認,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,是這股實學潮流的集大成之作。
如果沒有清軍入主中原,並在康雍乾時期實行倒退的政策,按照晚明的發展勢頭,中國並非沒有可能走上類似西歐的近代化之路。
可惜,歷史沒有如果。
明清易代之後,晚明重視科學技術的潮流就逐漸被掐斷了。
▲《天工開物》中的插畫。圖源:圖蟲創意授權
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在清初火了一陣子之後,突然間銷聲匿跡,完全絕版。
他本人在貧困中度過了晚年的時光,大約在康熙五年(1666年),離開了人世。臨終前,他把一生的經驗教訓,作為「宋氏家訓」留給子孫們:一不參加科舉,二不去做官,只在家鄉安心耕讀,以書香傳家。
也好,他死得倒是時候,看不到自己寄予厚望的書將被冷落到何種程度。
乾隆時期,朝廷以編修《四庫全書》的名義,對全國的圖書進行大規模的審查。原先流通的許多書籍,在這次號稱「偉大的文化工程」之後,就在歷史上無故「失蹤」了。
嚴格來說,《天工開物》並未被禁毀,它只是被四庫館臣置之不理。
這麼好的書,為何被官方無視?
原因有兩個:一個是《四庫全書》的收錄,沿襲傳統尊經重史的慣例,對科技書籍不感冒;另一個是,宋應星這本書中對明朝的推崇、對女真族的鄙夷,觸犯了政治禁區。
然而,不被《四庫全書》收錄本身並不是最可怕的,最可怕的是,不被收錄後的命運。
由於《四庫全書》的態度傳達了官方輿論導向,致使《天工開物》被無限上綱上線成為政治不合格的書籍。在政治正確的主導下,以及文化的權力控制下,再也沒有人敢印刷這本書了。
這一文化高壓的結果,導致《天工開物》在中國消失近300年。
弔詭的是,這本書在中國銷聲匿跡的同時,在另外的空間卻異常火爆。
《天工開物》在歐洲,被翻譯成12國語言,傳播甚廣。歐洲學者稱,這本書「直接推動了歐洲農業革命」。宋應星則被稱為「中國的狄德羅」。狄德羅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,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。
在日本,這本書從17世紀末傳入後,就火得一塌糊塗,不斷被再版和重印。因為這本書,日本還曾流行過富國濟民的「開物之學」。日本人將此書奉為「植產興業」的指南,非常實用。
一直到了民國時期,這本書「出口轉內銷」。中國人通過日本的版本,才知道我們原來有這麼偉大的一部書。
同樣的事情發生一次還不足以證明清朝統治者的愚蠢,必須讓它發生兩次才行。這是最可悲的地方。
時間已經到了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鴉片戰爭後,大清在天朝上國的良好幻覺中,挨了英國一頓暴揍。又是賠錢,又是割地,慘痛至極。
這一年,湖南人魏源的《海國圖志》在揚州刻印出版。
這部書第一次全面而系統地描述了天朝之外的世界狀況,不僅包括各國地理,還包括關於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產的儘可能完備的論述。
在大清新敗的時候,出版這樣一部大書,無疑是想為習慣了閉關鎖國的中國人,打開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戶。所謂「知己知彼,百戰不殆」,這條古訓,並不過時嘛。
然而,魏源還是太天真了。
甫一出版,頑固派的罵聲就撲面而來。他們無法接受書中對西方蠻夷的「讚美」之詞,他們的自尊心強到聽不進一句別國的好。在他們的心裡,鴉片戰爭輸了,但天朝還是天朝,蠻夷還是蠻夷,世界未曾因為一場戰爭而改變。
有官員主張將《海國圖志》付之一炬。
遭到無端非議的《海國圖志》,在國內僅印刷了1000冊左右,隨即就被列為禁書。
再後來,連談論這部書都成為禁忌。左宗棠曾無奈地指出,《海國圖志》問世20年,中國根本沒變樣,「事局如故」。
用史學家黃仁宇的話來說,萬曆十五年(1587年),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份。
江西人宋應星,就出生在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。
宋應星出生之時,家、國雙衰——比國家衰落得更快的是他的家族。從三代俱封尚書的高光家族,到黯淡無光的普通家族,只用了三四十年。
據說,宋應星少年天才,過目不忘。但這個本事對於他個人命運、家族命運的扭轉,毫無益處。
他一生最大的光榮,就是和哥哥宋應昇在江西鄉試中,雙雙考中舉人。
此後,他五次進京考進士,每次都當了炮灰。
沒辦法,縱有凌雲志,他一輩子也只能苟且在縣城教諭這樣無權無錢的職位上。
但他始終心有不甘,時常沒日沒夜、吭哧吭哧地寫書。
大概50歲的時候,他的書殺青了。這時,他告訴世人:
傷哉,貧也!欲購奇考證,而乏洛下之資;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,而缺陳思之館。隨其孤陋見聞,藏諸方寸而寫之,豈有當哉!
翻譯過來就是,貧窮限制了我,我沒有錢購買參考資料,也沒有條件邀集同人集思廣議,只能寫成這個樣子了,能不傷心嗎?
還好,他有個好朋友塗伯聚,幫他把書印刷出版了。
這一年是1637年。
很多很多年以後,歷史學家說起1637年,總會強調這是一個奇特的年份。這一年,東西方分別出版了一本深刻影響人類歷史的書。
一本是歐洲近代哲學奠基人笛卡爾的《方法論》,另一本,正是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。
令人嗟嘆的是,這兩本偉大之書的命運截然不同。前者樹立起理性主義的大旗,藉助科學實踐掀起產業革命,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。
而後者,卻開啟了一段過山車般的奇幻傳播旅程。
▲宋應星,一個奇人寫了一本奇書。圖源:圖蟲創意授權
宋應星是個奇人。在《天工開物》問世大約300年後,地質學家丁文江如此評價他:
士大夫之心理,內容乾燥荒蕪,等於不毛之沙漠,宋氏獨自辟門徑,一反明儒陋習,就人民日用飲食器具而究其源,其活力之偉,結構之大,觀察之富,有明一代,一人而已。
這幾乎是把宋應星捧上天了。
《天工開物》到底是本什麼書,會讓宋應星贏得「有明一代,一人而已」的極高讚譽?
簡單說,這本書總結了大量農業、工業中所需要的培育、生產知識,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科普體系,並有意識使用數據記載,使整本書更加實用。
西方人稱這本書為「中國十七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」。
這本書初版時,在國內的銷量並不好。沒幾年,大明亡了。清初,有個叫楊素卿的福建書商發現了這本書,並把他包裝成了暢銷書。
當時很多人因此知道並讀到《天工開物》。
宋應星撰述此書,目的是通過實學,來達到富國強民。他的骨子裡還是有為時代把脈,並開出藥方的想法。
晚明的思想、經濟以及科技發展勢頭,實際上並不落後於西歐。當時,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產生,一些思想家呼籲人性解放,另一些人倡導實用主義,擺脫既往的道德話語束縛,不再將科學技術視為「奇技淫巧」。
他們通過田野考察、收集整理、記錄數據、歸納分類等方法,寫出了一批科技著作。比如,地理學有徐霞客的《遊記》,藥物學有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,水利工程有潘季馴的《河防一覽》,農學有徐光啟的《農政全書》等等。
大家公認,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,是這股實學潮流的集大成之作。
如果沒有清軍入主中原,並在康雍乾時期實行倒退的政策,按照晚明的發展勢頭,中國並非沒有可能走上類似西歐的近代化之路。
可惜,歷史沒有如果。
明清易代之後,晚明重視科學技術的潮流就逐漸被掐斷了。
▲《天工開物》中的插畫。圖源:圖蟲創意授權
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在清初火了一陣子之後,突然間銷聲匿跡,完全絕版。
他本人在貧困中度過了晚年的時光,大約在康熙五年(1666年),離開了人世。臨終前,他把一生的經驗教訓,作為「宋氏家訓」留給子孫們:一不參加科舉,二不去做官,只在家鄉安心耕讀,以書香傳家。
也好,他死得倒是時候,看不到自己寄予厚望的書將被冷落到何種程度。
乾隆時期,朝廷以編修《四庫全書》的名義,對全國的圖書進行大規模的審查。原先流通的許多書籍,在這次號稱「偉大的文化工程」之後,就在歷史上無故「失蹤」了。
嚴格來說,《天工開物》並未被禁毀,它只是被四庫館臣置之不理。
這麼好的書,為何被官方無視?
原因有兩個:一個是《四庫全書》的收錄,沿襲傳統尊經重史的慣例,對科技書籍不感冒;另一個是,宋應星這本書中對明朝的推崇、對女真族的鄙夷,觸犯了政治禁區。
然而,不被《四庫全書》收錄本身並不是最可怕的,最可怕的是,不被收錄後的命運。
由於《四庫全書》的態度傳達了官方輿論導向,致使《天工開物》被無限上綱上線成為政治不合格的書籍。在政治正確的主導下,以及文化的權力控制下,再也沒有人敢印刷這本書了。
這一文化高壓的結果,導致《天工開物》在中國消失近300年。
弔詭的是,這本書在中國銷聲匿跡的同時,在另外的空間卻異常火爆。
《天工開物》在歐洲,被翻譯成12國語言,傳播甚廣。歐洲學者稱,這本書「直接推動了歐洲農業革命」。宋應星則被稱為「中國的狄德羅」。狄德羅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,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。
在日本,這本書從17世紀末傳入後,就火得一塌糊塗,不斷被再版和重印。因為這本書,日本還曾流行過富國濟民的「開物之學」。日本人將此書奉為「植產興業」的指南,非常實用。
一直到了民國時期,這本書「出口轉內銷」。中國人通過日本的版本,才知道我們原來有這麼偉大的一部書。
同樣的事情發生一次還不足以證明清朝統治者的愚蠢,必須讓它發生兩次才行。這是最可悲的地方。
時間已經到了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鴉片戰爭後,大清在天朝上國的良好幻覺中,挨了英國一頓暴揍。又是賠錢,又是割地,慘痛至極。
這一年,湖南人魏源的《海國圖志》在揚州刻印出版。
這部書第一次全面而系統地描述了天朝之外的世界狀況,不僅包括各國地理,還包括關於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產的儘可能完備的論述。
在大清新敗的時候,出版這樣一部大書,無疑是想為習慣了閉關鎖國的中國人,打開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戶。所謂「知己知彼,百戰不殆」,這條古訓,並不過時嘛。
然而,魏源還是太天真了。
甫一出版,頑固派的罵聲就撲面而來。他們無法接受書中對西方蠻夷的「讚美」之詞,他們的自尊心強到聽不進一句別國的好。在他們的心裡,鴉片戰爭輸了,但天朝還是天朝,蠻夷還是蠻夷,世界未曾因為一場戰爭而改變。
有官員主張將《海國圖志》付之一炬。
遭到無端非議的《海國圖志》,在國內僅印刷了1000冊左右,隨即就被列為禁書。
再後來,連談論這部書都成為禁忌。左宗棠曾無奈地指出,《海國圖志》問世20年,中國根本沒變樣,「事局如故」。
 呂純弘 • 3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