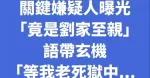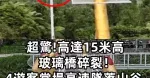4/8
下一頁
此戰一勝,至今封神

4/8
▲西張線227國道,沿著張騫出使西域、霍去病馬踏匈奴的路線。圖源:圖蟲創意授權
同年夏季,祁連山下芳草萋萋,漢軍兵分兩路,再次出征。
東路軍由名將李廣領銜,帶四千騎兵打頭陣。此時,張騫已出使西域歸來,被封為博望侯,帶兵一萬作為援軍。東路軍的主要目標是牽制漠南的匈奴左賢王部,避免其支援河西。
奈何李廣難封,依舊不走運。
東路軍的李廣軍北出漢塞幾百里後,與匈奴左賢王的四萬騎兵不期而遇,雙方在廣闊無垠的草原上展開激戰。
面對十倍於己的匈奴大軍,李廣經驗老到,讓漢軍立即組成圜形陣,將輜重車連接起來作為外圍的屏障,弓箭手以此為掩護進行射擊。為了穩定軍心,李廣還命令自己的兒子李敢帶頭衝鋒,殺到匈奴陣前。
李廣所部經過一天的苦戰,幾乎損失殆盡,而且隊友很不給力,這時,張騫的軍隊才遲遲趕到。匈奴左賢王看到漢軍有增援,便解圍而去,但東路軍也就未能建功,遲到的張騫回朝後被廢為庶人,後來才被再次起用,二使西域。
劍指祁連山的西路軍方面,有一支軍隊由公孫敖率領,但是他在沙漠中迷路了,愣是找不著西。
關鍵時刻,還得看霍去病。
霍去病的軍隊從北地郡(今甘肅慶陽)出發後,仍是採取大迂迴的作戰方式,渡過黃河,橫穿大漠,至居延澤(今內蒙古額濟納旗),經過小月氏的領地,再轉向東南,長驅直入二千餘里,繞到匈奴渾邪王與休屠王部的後方。
在霍去病的突襲下,渾邪王與休屠王損失慘重。史載,與霍去病率領的漢軍在祁連山區相遇後,匈奴二王所部被斬殺三萬多人。他們半年之內被霍去病痛揍了兩次。
這是河西之戰的決定性勝利。此後,占據河西的匈奴渾邪王、休屠王再無還手之力,憤怒的伊稚斜單于聽說他們戰敗,甚至要誅殺他們(「怒渾邪王、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,欲召誅之」)。
幾個月後,秋風蕭瑟之際,害怕被殺的渾邪王與休屠王相約向漢朝投降。漢武帝便派得勝歸來的霍去病率軍前往受降。
半路上,休屠王慫了,突然反悔,不願降漢。於是,渾邪王殺死休屠王,吞併他的部屬後再去見霍去病。
匈奴人渡過黃河後,見霍去病的軍隊這麼大陣仗,嚇傻了,渾邪王的一些部眾意圖逃跑。霍去病毫不遲疑,率領精銳部隊馳入匈奴營中,見到渾邪王后,將企圖逃跑的匈奴人斬殺,招降四萬多人。
漢武帝命令將渾邪王遷至長安,將其部眾分別安置在隴西、北地、上郡、朔方、雲中等五郡之外,號稱「五屬國」。之後,漢朝在祁連山下的河西走廊設立四個郡,分別為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敦煌,史稱「河西四郡」。
至此,匈奴人結束了在河西持續半個多世紀的統治,河西盡歸於漢。匈奴人失去了家園,紛紛唱起那首悲傷的歌謠:「失我焉支山,使我婦女無顏色;失我祁連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。」
漢朝的使者、商隊、軍隊,從此可以暢通無阻地通過河西走廊,奔赴西域,在祁連山放牧的小月氏人也歸附於漢,後與河西漢人融合。立下大功的霍去病看上了山谷間的牧場,在此始創馬場,即山丹軍馬場,該馬場至今仍是我國乃至亞洲最大的軍馬繁育基地。
漢武帝是個文化人,他為河西四郡取名,各有其寓意。比如「敦煌」,敦,大也,煌,盛也。又如「武威」,是為了彰顯大漢帝國的武功軍威。
黑河之畔的張掖郡,則是取「張國臂掖,以通西域」之意,更具體言之,就是斷匈奴之臂,張中國之掖。
從地圖上看,河西走廊如同一隻伸向西域的手臂,而其南邊逶迤不盡的祁連山,就是構成這隻鐵臂的筋骨,一路拱衛著沿途的道路和綠洲,用雪水哺育大大小小的城鎮。
可以說,若無祁連山脈,河西走廊的歷史也會被改寫。
河西之戰後,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,漢武帝調集精兵十萬,由衛青和霍去病統領,北上漠北,與匈奴決戰。其中,霍去病軍北進兩千多里,殲滅匈奴七萬人,「封狼居胥山,禪於姑衍」,一路追擊到貝加爾湖後班師回朝。
漠北之戰後,「匈奴遠遁,而漠南無王庭」,威脅漢朝北境百餘年的匈奴邊患基本解決。
遺憾的是,漠北決戰僅僅過去兩年,戎馬倥傯的霍去病便英年早逝。
霍去病去世後,漢武帝賜其陪葬茂陵。下葬時,漢武帝特意調遣河西的鐵甲軍列陣成隊,從長安一直排到茂陵東的霍去病墓。
霍去病的墓被修建成祁連山的形狀,墓前置「馬踏匈奴」石像,以表彰他在河西之戰中「斷匈奴之臂」的赫赫戰功。
英傑早逝,但千載雄名永世不滅。
同年夏季,祁連山下芳草萋萋,漢軍兵分兩路,再次出征。
東路軍由名將李廣領銜,帶四千騎兵打頭陣。此時,張騫已出使西域歸來,被封為博望侯,帶兵一萬作為援軍。東路軍的主要目標是牽制漠南的匈奴左賢王部,避免其支援河西。
奈何李廣難封,依舊不走運。
東路軍的李廣軍北出漢塞幾百里後,與匈奴左賢王的四萬騎兵不期而遇,雙方在廣闊無垠的草原上展開激戰。
面對十倍於己的匈奴大軍,李廣經驗老到,讓漢軍立即組成圜形陣,將輜重車連接起來作為外圍的屏障,弓箭手以此為掩護進行射擊。為了穩定軍心,李廣還命令自己的兒子李敢帶頭衝鋒,殺到匈奴陣前。
李廣所部經過一天的苦戰,幾乎損失殆盡,而且隊友很不給力,這時,張騫的軍隊才遲遲趕到。匈奴左賢王看到漢軍有增援,便解圍而去,但東路軍也就未能建功,遲到的張騫回朝後被廢為庶人,後來才被再次起用,二使西域。
劍指祁連山的西路軍方面,有一支軍隊由公孫敖率領,但是他在沙漠中迷路了,愣是找不著西。
關鍵時刻,還得看霍去病。
霍去病的軍隊從北地郡(今甘肅慶陽)出發後,仍是採取大迂迴的作戰方式,渡過黃河,橫穿大漠,至居延澤(今內蒙古額濟納旗),經過小月氏的領地,再轉向東南,長驅直入二千餘里,繞到匈奴渾邪王與休屠王部的後方。
在霍去病的突襲下,渾邪王與休屠王損失慘重。史載,與霍去病率領的漢軍在祁連山區相遇後,匈奴二王所部被斬殺三萬多人。他們半年之內被霍去病痛揍了兩次。
這是河西之戰的決定性勝利。此後,占據河西的匈奴渾邪王、休屠王再無還手之力,憤怒的伊稚斜單于聽說他們戰敗,甚至要誅殺他們(「怒渾邪王、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,欲召誅之」)。
幾個月後,秋風蕭瑟之際,害怕被殺的渾邪王與休屠王相約向漢朝投降。漢武帝便派得勝歸來的霍去病率軍前往受降。
半路上,休屠王慫了,突然反悔,不願降漢。於是,渾邪王殺死休屠王,吞併他的部屬後再去見霍去病。
匈奴人渡過黃河後,見霍去病的軍隊這麼大陣仗,嚇傻了,渾邪王的一些部眾意圖逃跑。霍去病毫不遲疑,率領精銳部隊馳入匈奴營中,見到渾邪王后,將企圖逃跑的匈奴人斬殺,招降四萬多人。
漢武帝命令將渾邪王遷至長安,將其部眾分別安置在隴西、北地、上郡、朔方、雲中等五郡之外,號稱「五屬國」。之後,漢朝在祁連山下的河西走廊設立四個郡,分別為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敦煌,史稱「河西四郡」。
至此,匈奴人結束了在河西持續半個多世紀的統治,河西盡歸於漢。匈奴人失去了家園,紛紛唱起那首悲傷的歌謠:「失我焉支山,使我婦女無顏色;失我祁連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。」
漢朝的使者、商隊、軍隊,從此可以暢通無阻地通過河西走廊,奔赴西域,在祁連山放牧的小月氏人也歸附於漢,後與河西漢人融合。立下大功的霍去病看上了山谷間的牧場,在此始創馬場,即山丹軍馬場,該馬場至今仍是我國乃至亞洲最大的軍馬繁育基地。
漢武帝是個文化人,他為河西四郡取名,各有其寓意。比如「敦煌」,敦,大也,煌,盛也。又如「武威」,是為了彰顯大漢帝國的武功軍威。
黑河之畔的張掖郡,則是取「張國臂掖,以通西域」之意,更具體言之,就是斷匈奴之臂,張中國之掖。
從地圖上看,河西走廊如同一隻伸向西域的手臂,而其南邊逶迤不盡的祁連山,就是構成這隻鐵臂的筋骨,一路拱衛著沿途的道路和綠洲,用雪水哺育大大小小的城鎮。
可以說,若無祁連山脈,河西走廊的歷史也會被改寫。
河西之戰後,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,漢武帝調集精兵十萬,由衛青和霍去病統領,北上漠北,與匈奴決戰。其中,霍去病軍北進兩千多里,殲滅匈奴七萬人,「封狼居胥山,禪於姑衍」,一路追擊到貝加爾湖後班師回朝。
漠北之戰後,「匈奴遠遁,而漠南無王庭」,威脅漢朝北境百餘年的匈奴邊患基本解決。
遺憾的是,漠北決戰僅僅過去兩年,戎馬倥傯的霍去病便英年早逝。
霍去病去世後,漢武帝賜其陪葬茂陵。下葬時,漢武帝特意調遣河西的鐵甲軍列陣成隊,從長安一直排到茂陵東的霍去病墓。
霍去病的墓被修建成祁連山的形狀,墓前置「馬踏匈奴」石像,以表彰他在河西之戰中「斷匈奴之臂」的赫赫戰功。
英傑早逝,但千載雄名永世不滅。
 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